Þ«ÇÒÇèÚƒôÚØ×Õ¡ÉÒÇïõ©¡þÜäÒÇèÚøúõ©ÇÒÇï´╝îµêæÕÇæµ£âµÇØÞÇâÕê░Õ║òõ©ìÞâ¢Þó½Õê║þá┤þÜäþø¥ÕÆîÞâ¢Õê║þá┤õ©ÇÕêçþÜäþƒøÞâ¢ÕɪÕÉîµÖéÕ¡ÿÕ£¿ÒÇéþ£ïõ╝╝Õ░ìþ½ïÒÇüþƒøþø¥þÜäõ║ïþë®´╝îÞâ¢ÕɪÕ░çõ╣ïÞ×ìÕÉê´╝ƒÚÜ¿ÞæùÕ╣┤õ╗úþÜäµø┤Þ┐¡ÒÇüµûçÕîûþÜäÞ¢ëÞ«è´╝îÞ¿▒ÕñÜõ║ïþë®þÜäµ£¼Þ│¬Úâ¢þÖ╝þöƒõ║åÞíØþ¬ü´╝îÕÅñÕà©ÞêçþÅ¥õ╗úÒÇüµ│ÑÕ£ƒÕÆîµ░┤µ│ÑÒÇüõ¢øµ│òÞêçµ¢«µÁüÚƒ│µ¿éÒÇéþƒøþø¥µÿ»µ║ɵ║Éõ©ìþÁòþÜä´╝îõ¢åÕëÁµäÅõ║ªþäÂÒÇéÕ£¿õ║║ÕÇæþÜäÕëÁÚÇáÕèøõ©ïþöóþöƒõ║åþƒøþø¥þ¥ÄÕ¡©´╝îÕæèÞ¿┤µêæÕÇæÒÇîÕ┐àþäÂÒÇìõ©ªõ©ìÕ┐àþäÂÒÇéµêæÕÇæÕ░çÕ¥×7ÚûÇÞùØÞíô´╝îÕêåõ║½ÚÇÖþ¿«ÚØ×Õû«õ©ÇþÜäþ¥ÄÚ║ùÒÇé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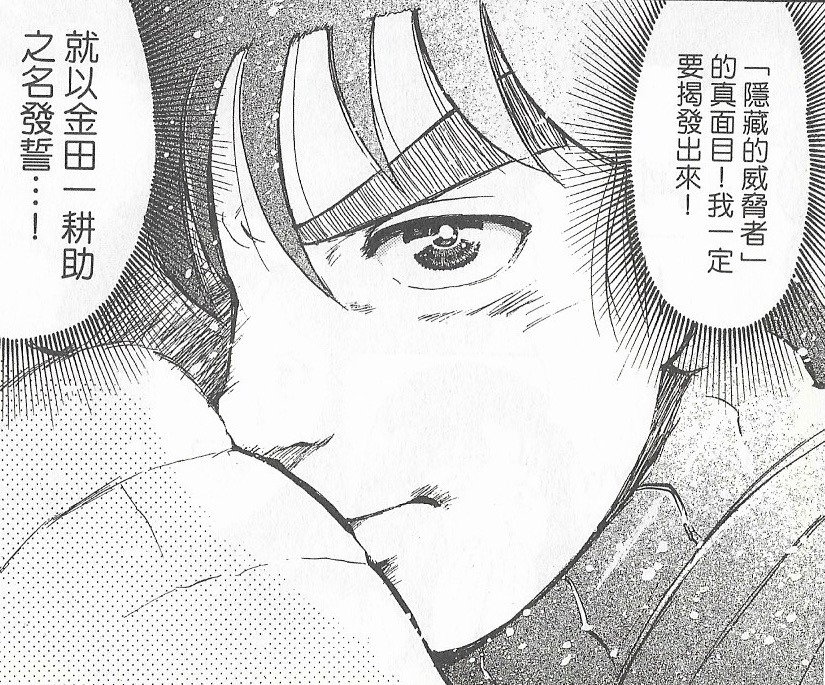
.jpe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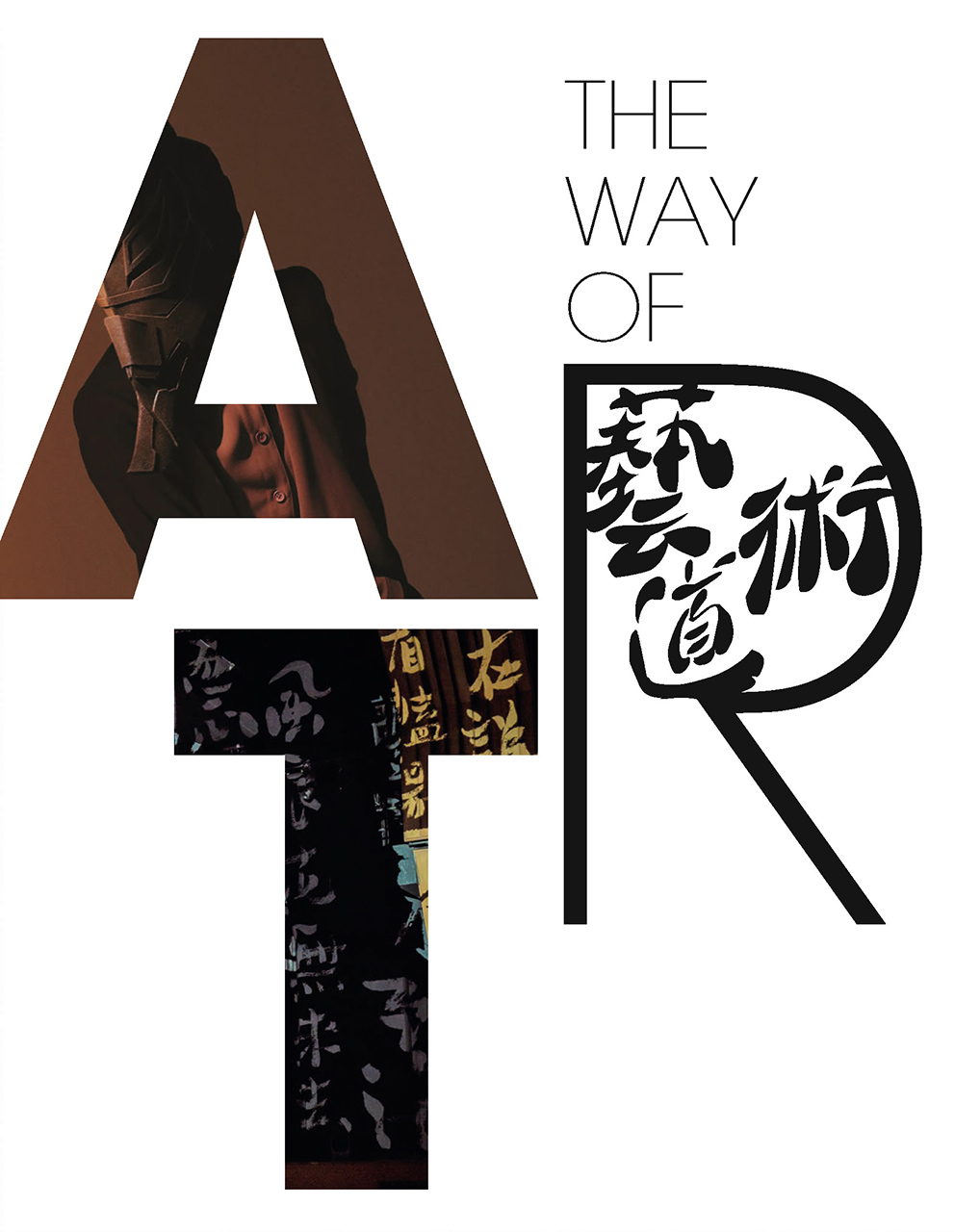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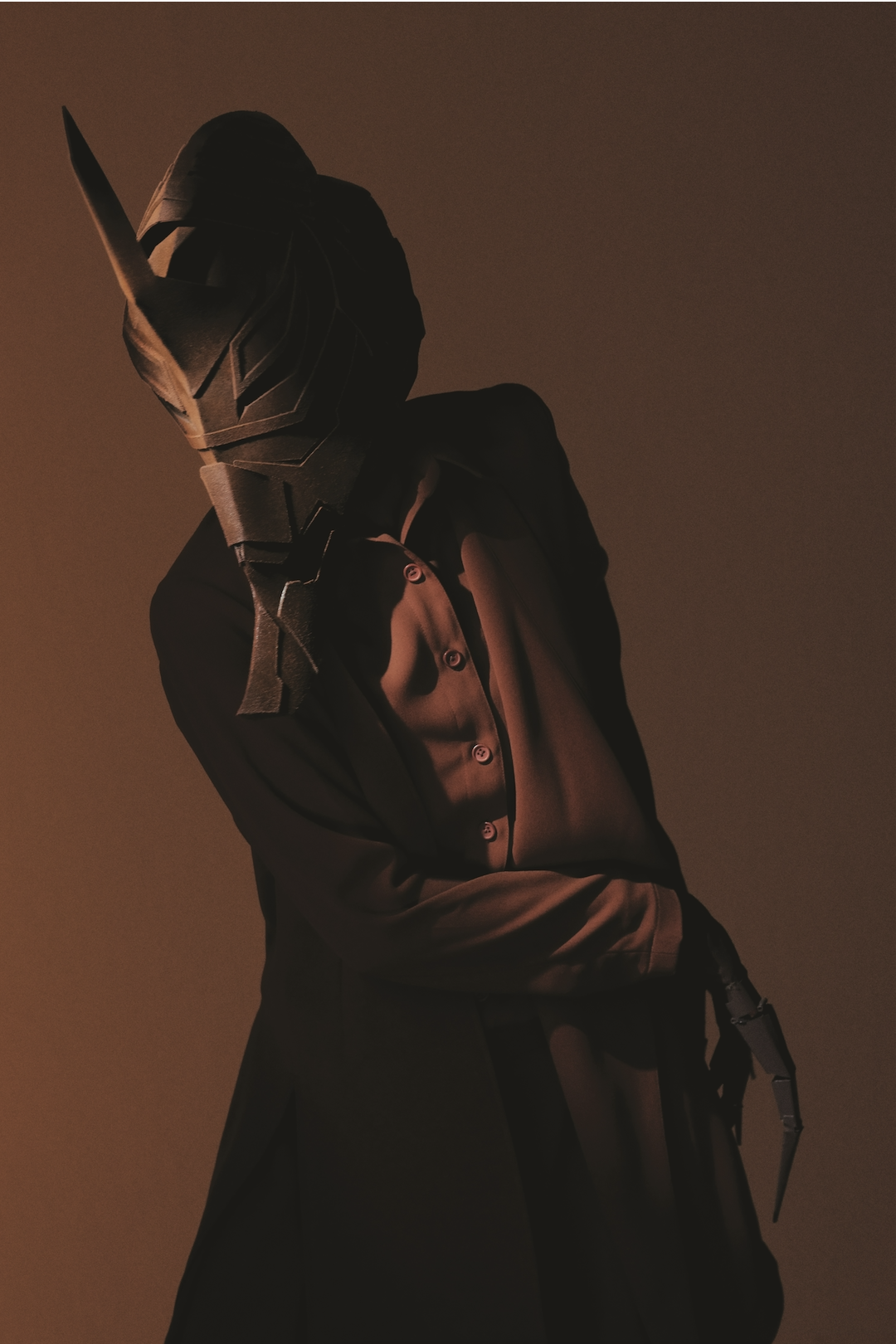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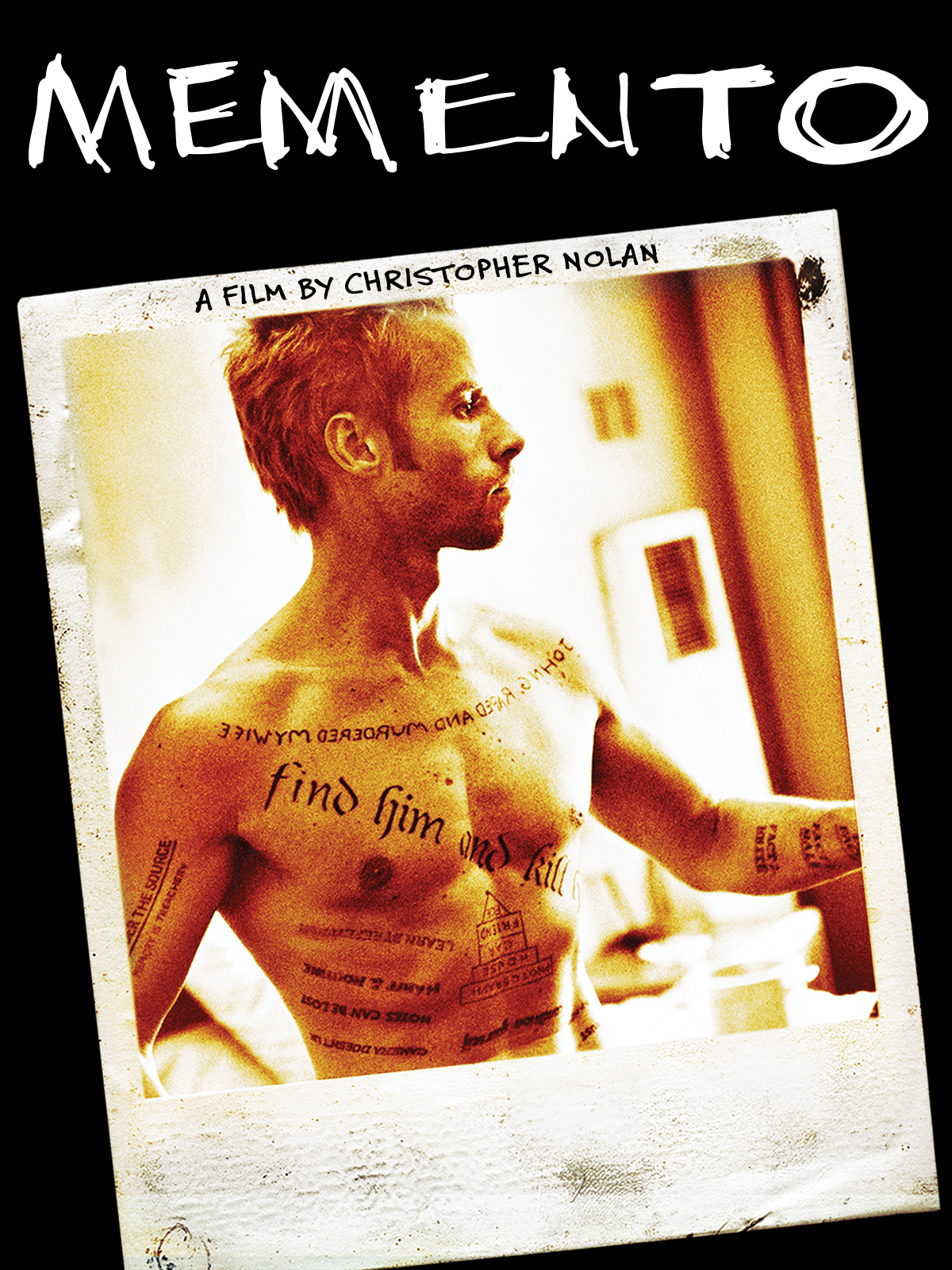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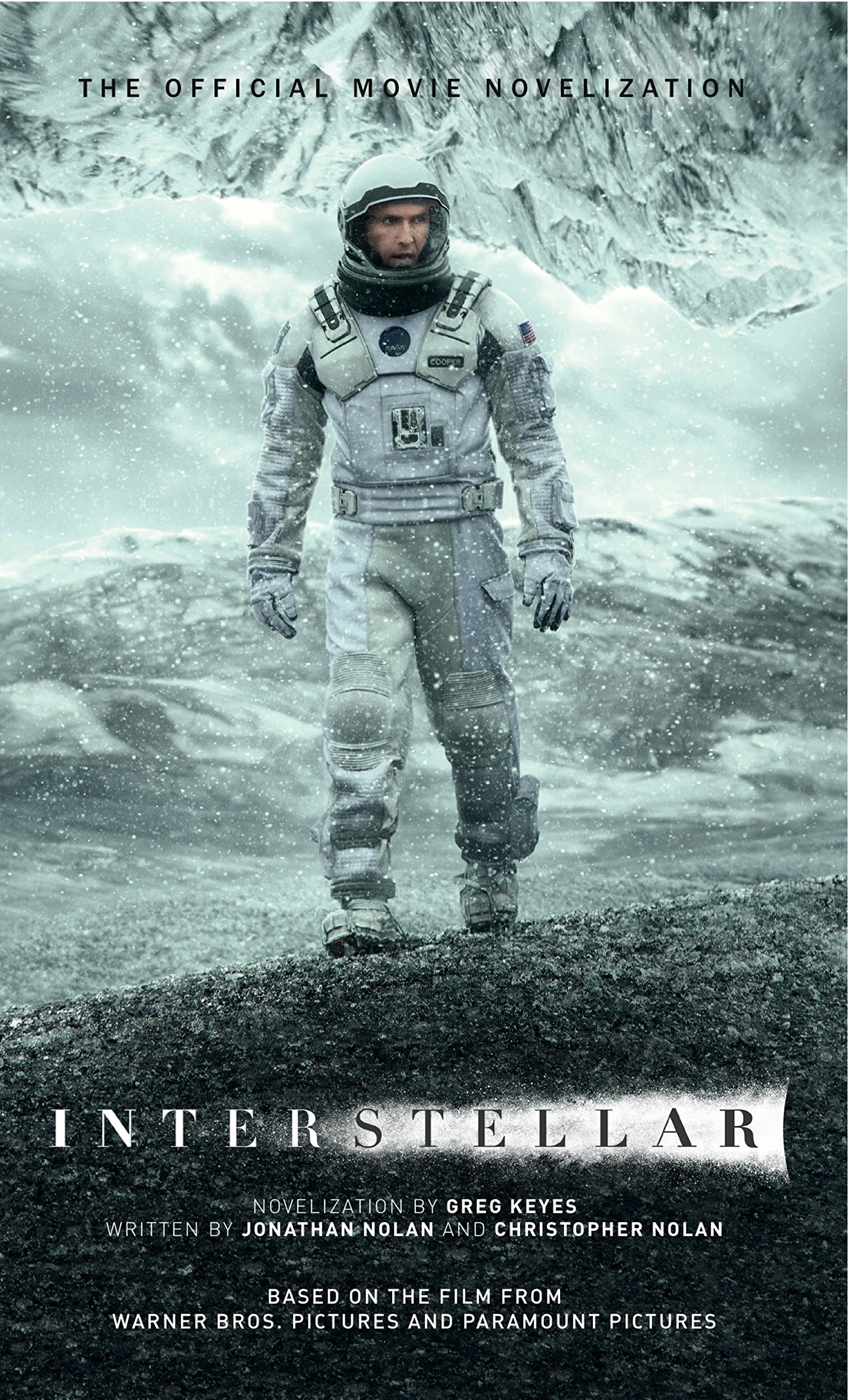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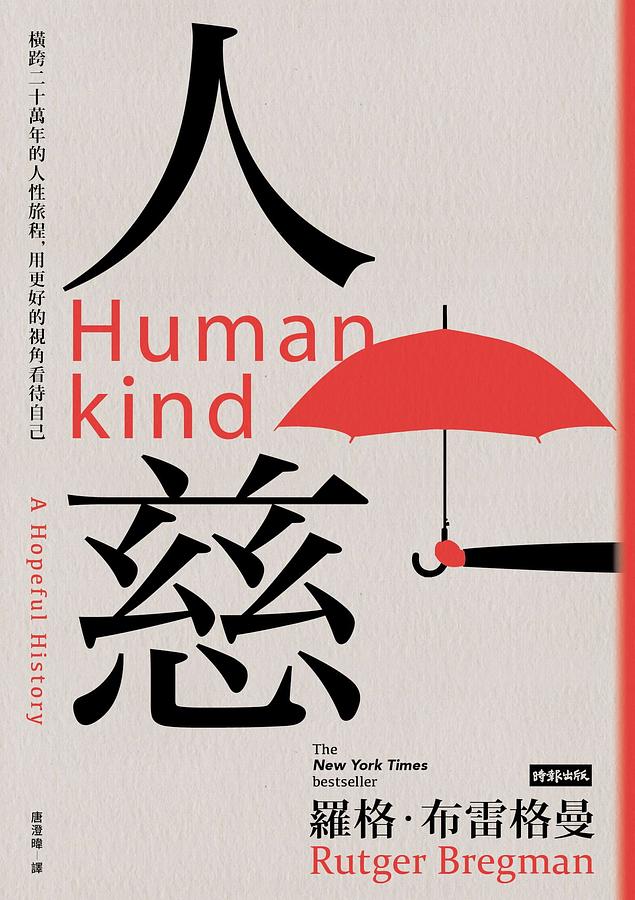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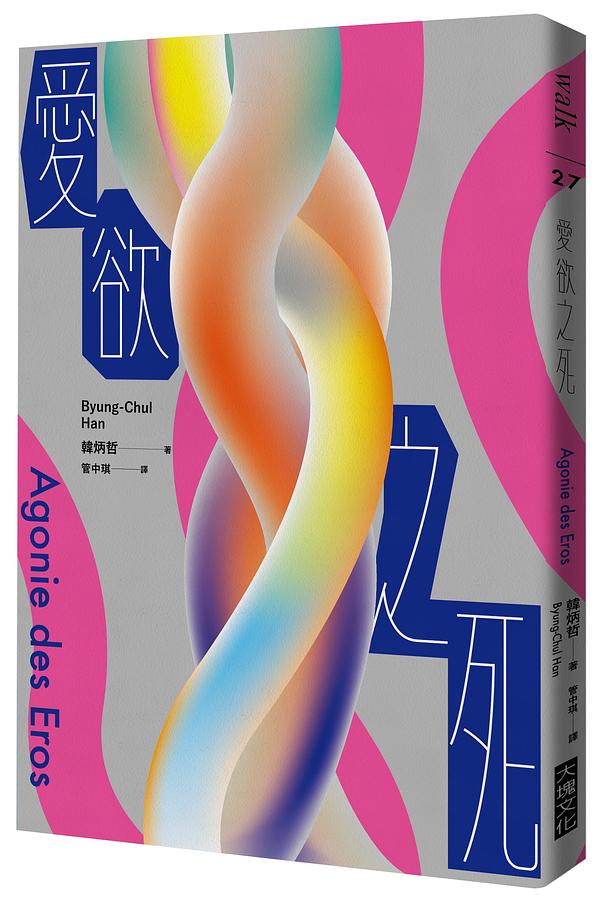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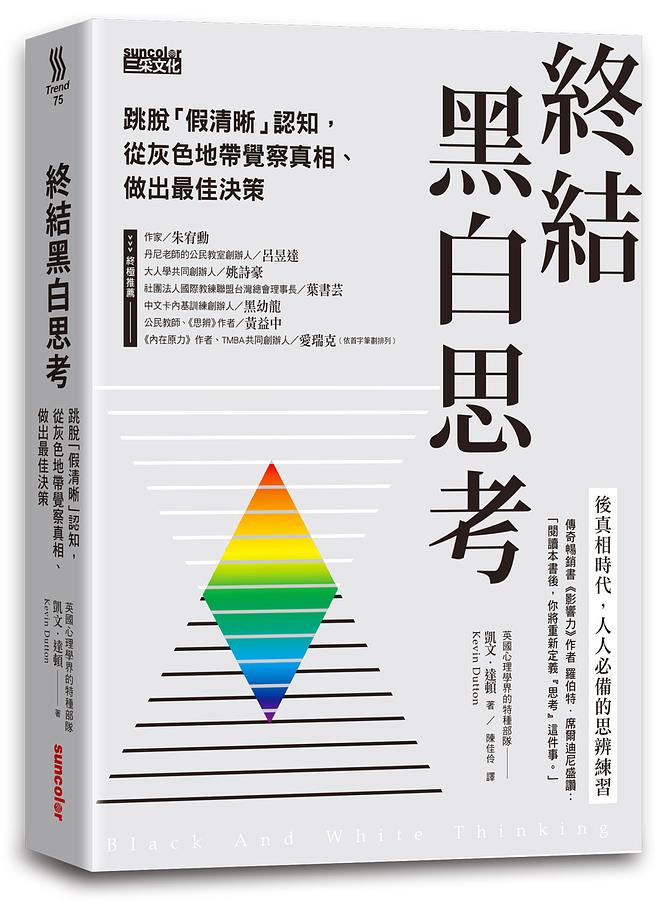

.jpg)